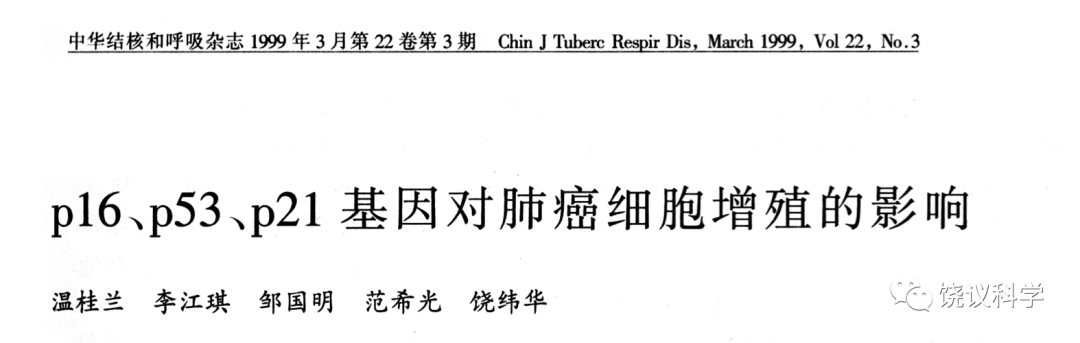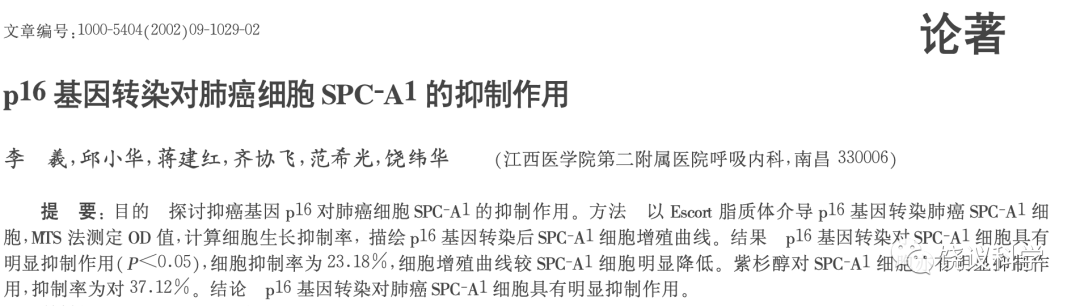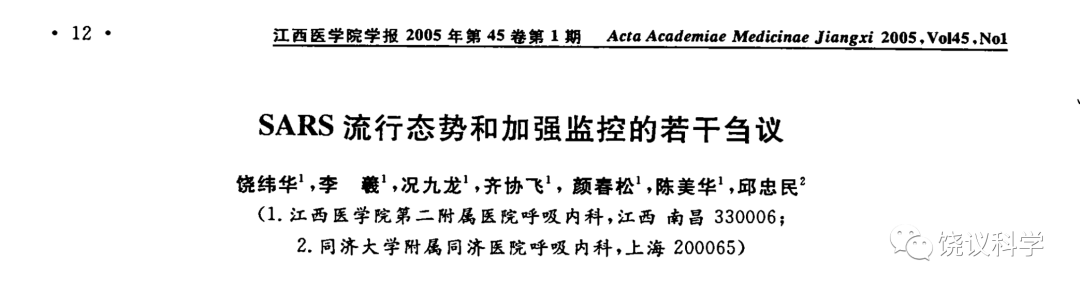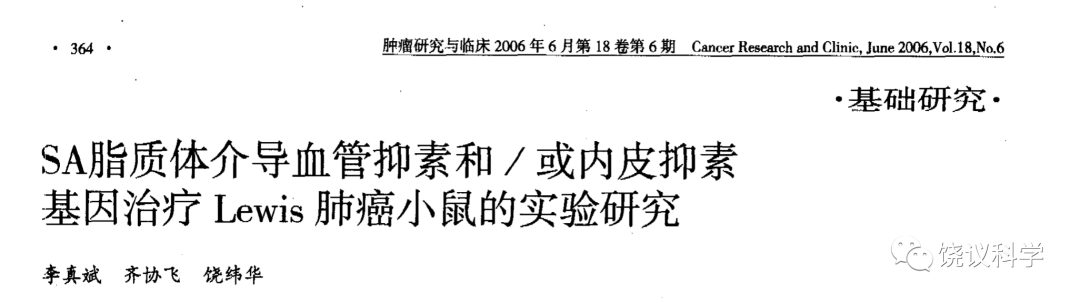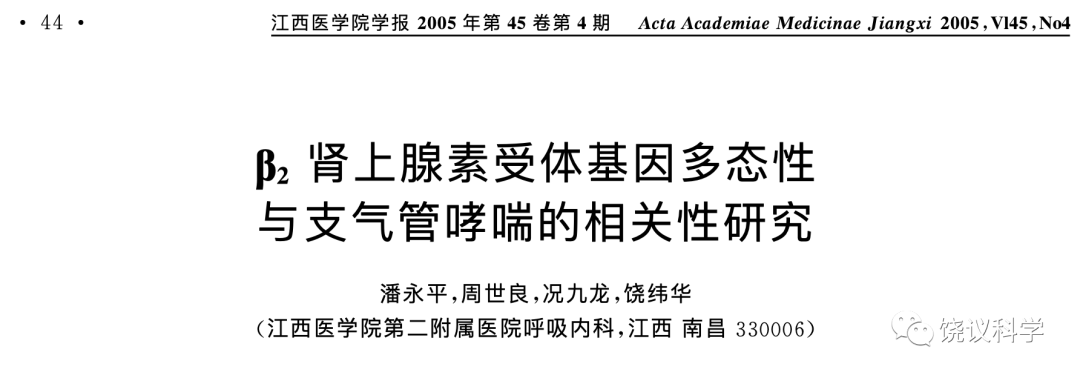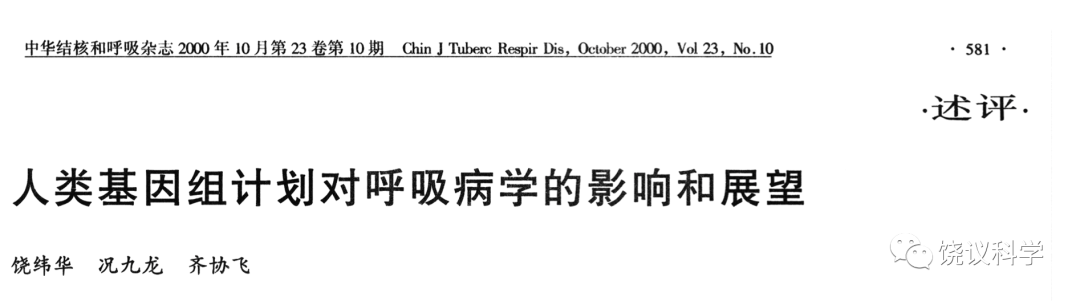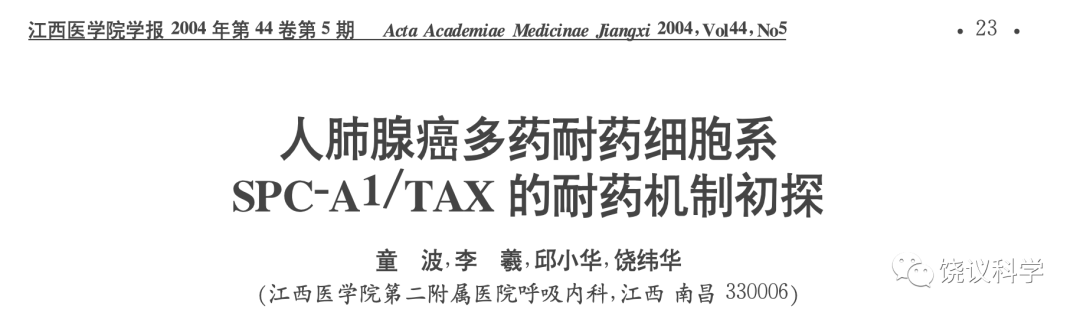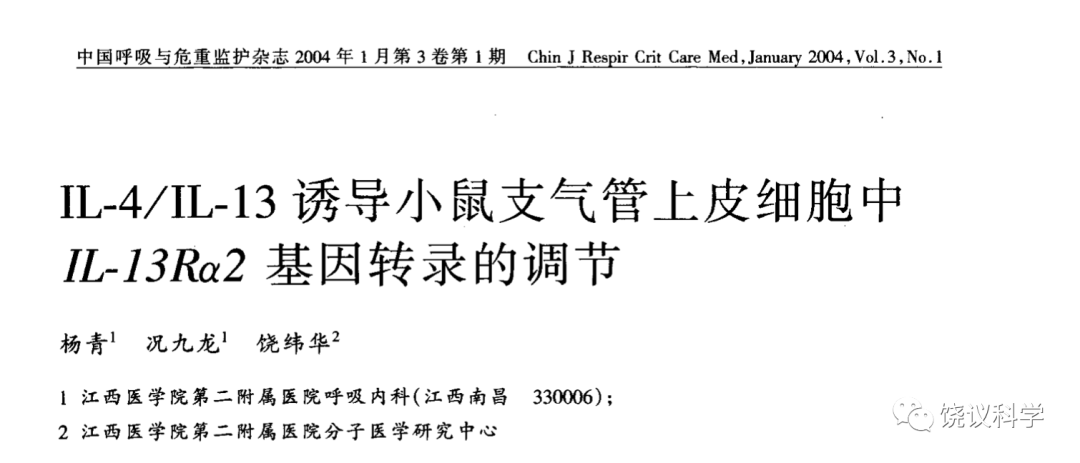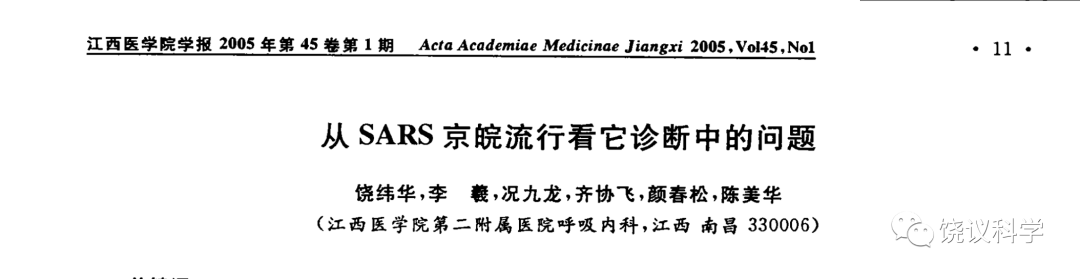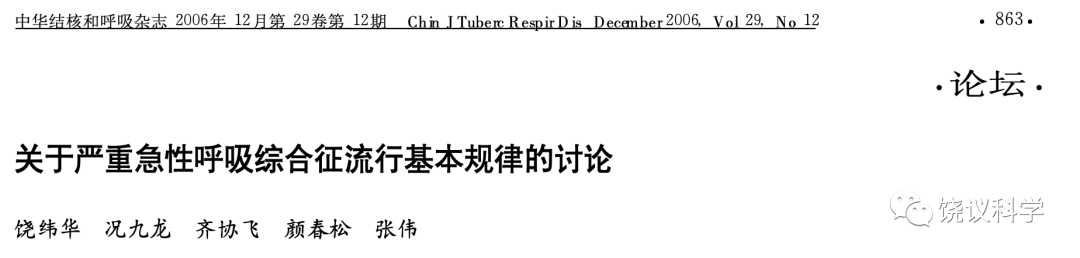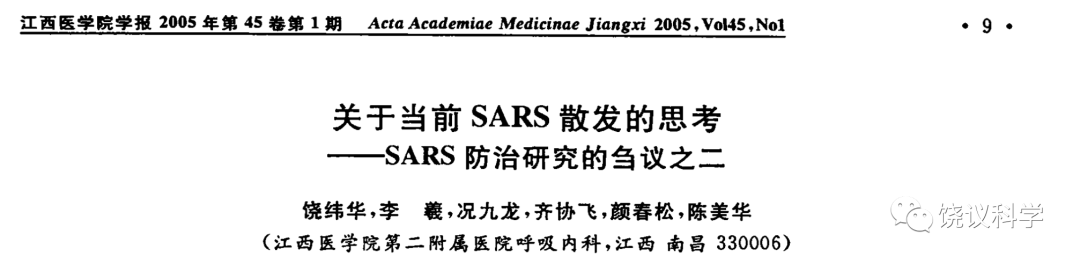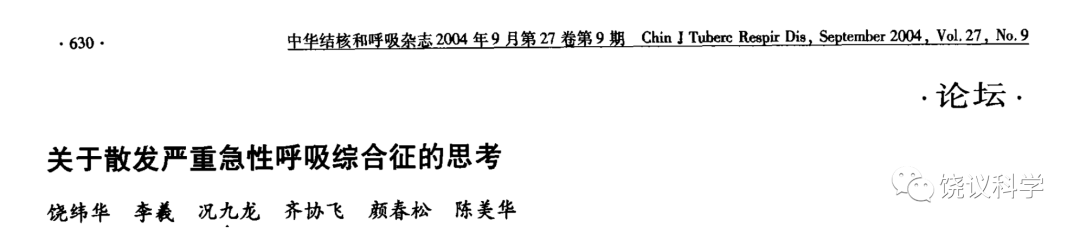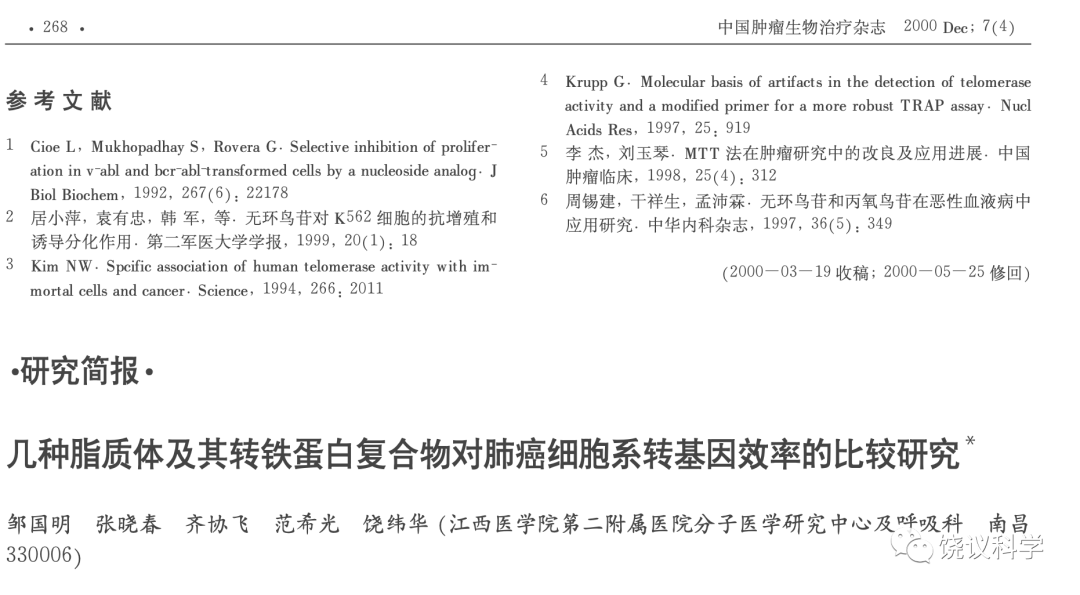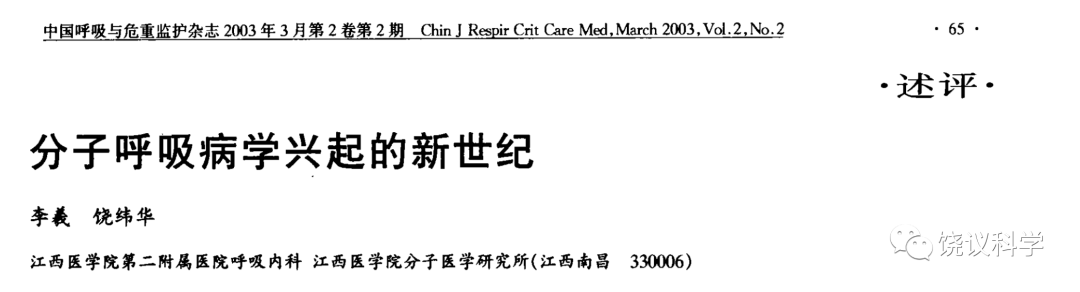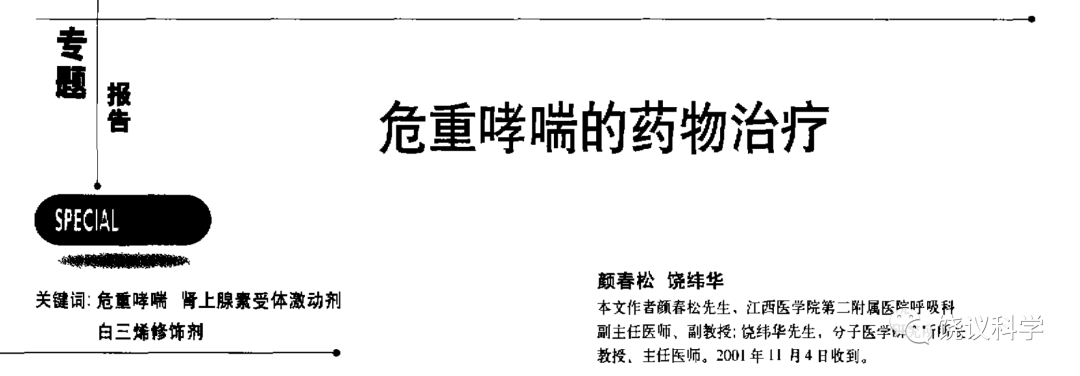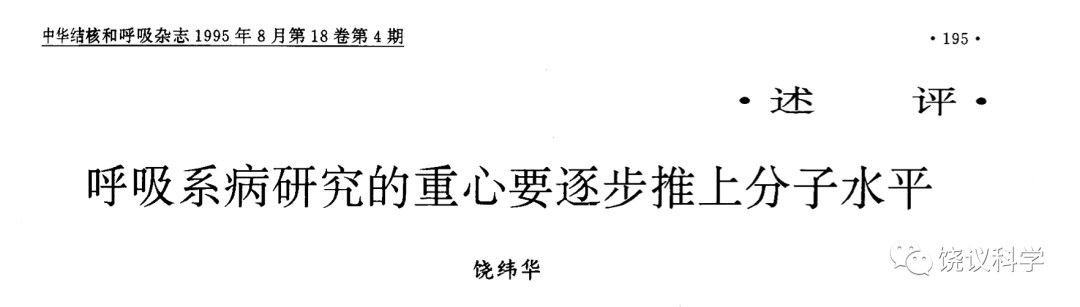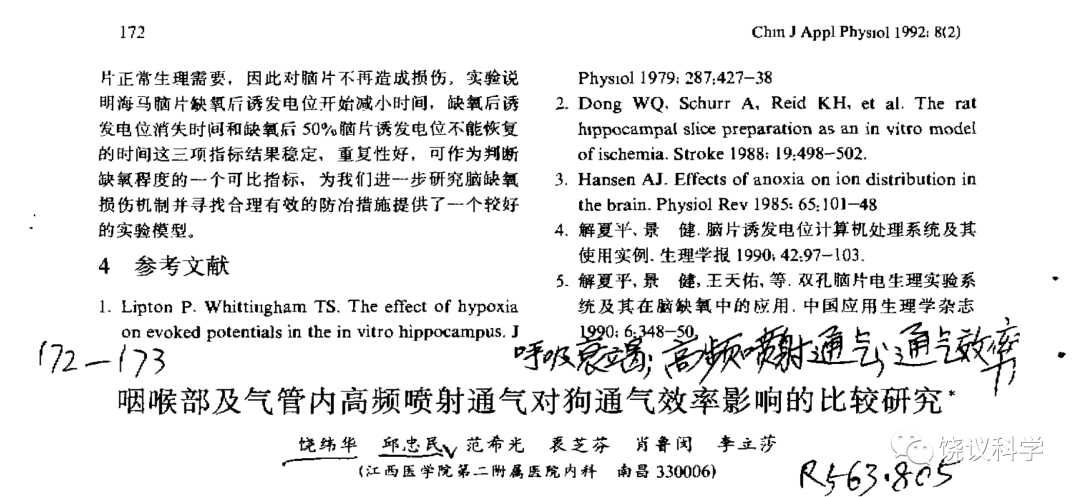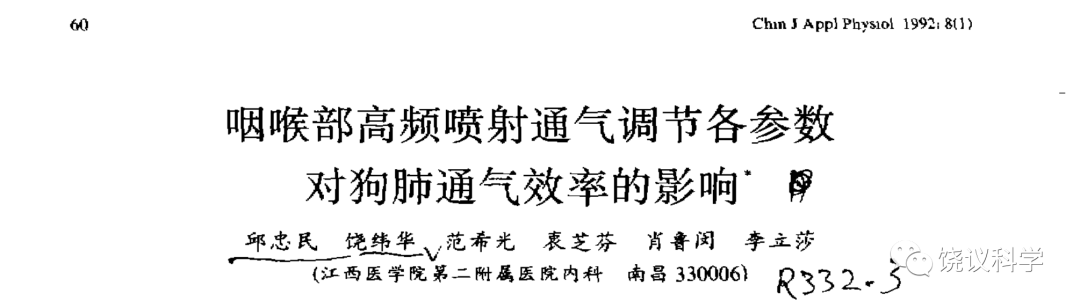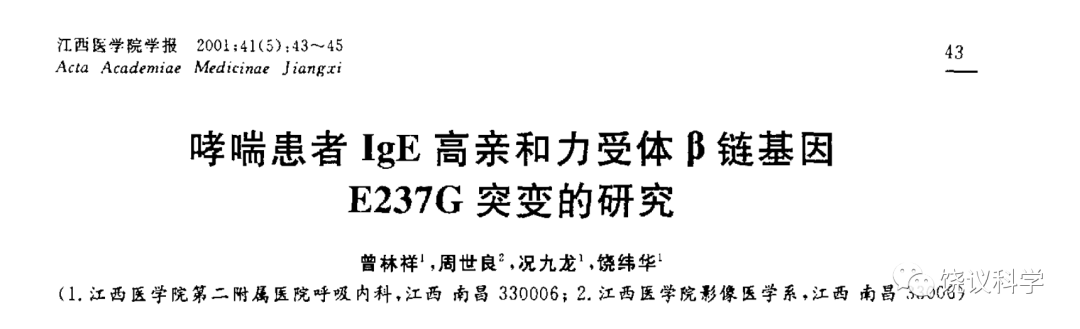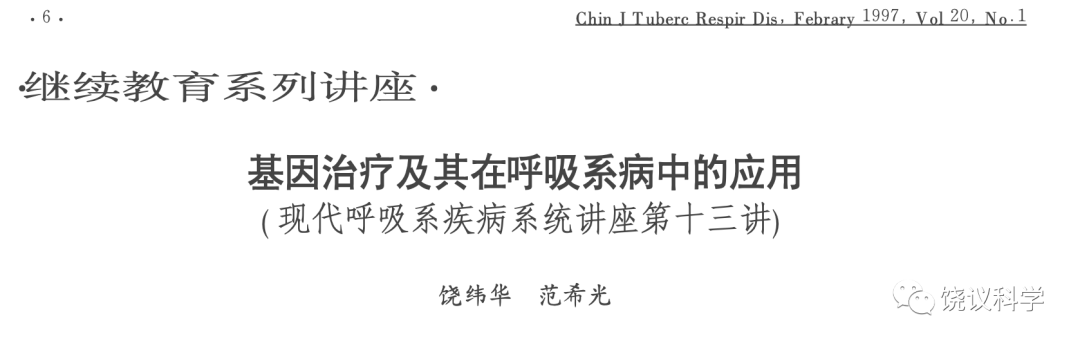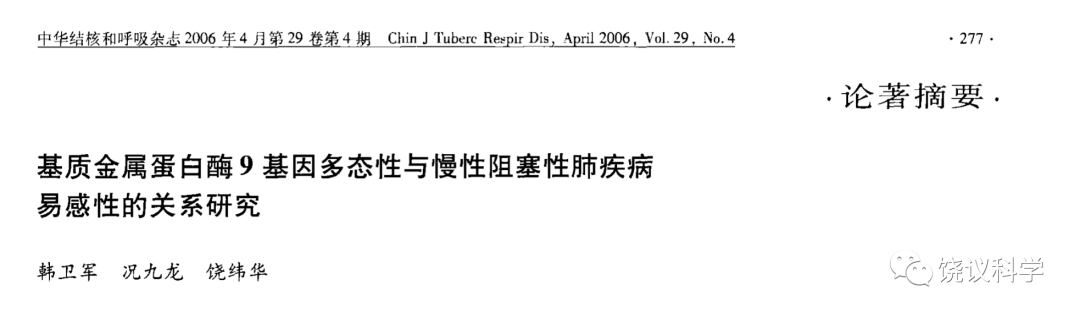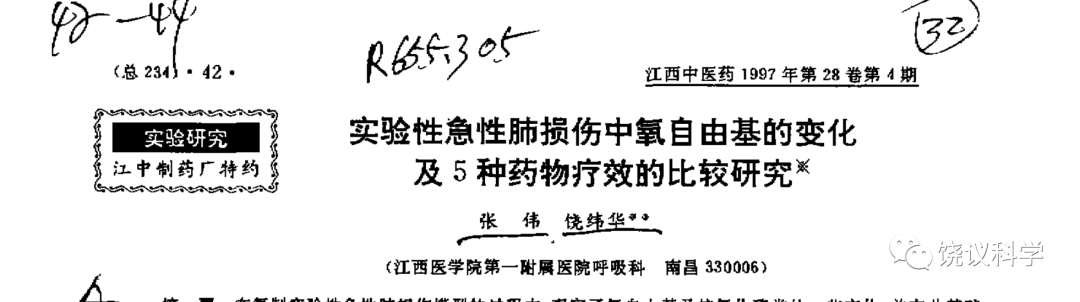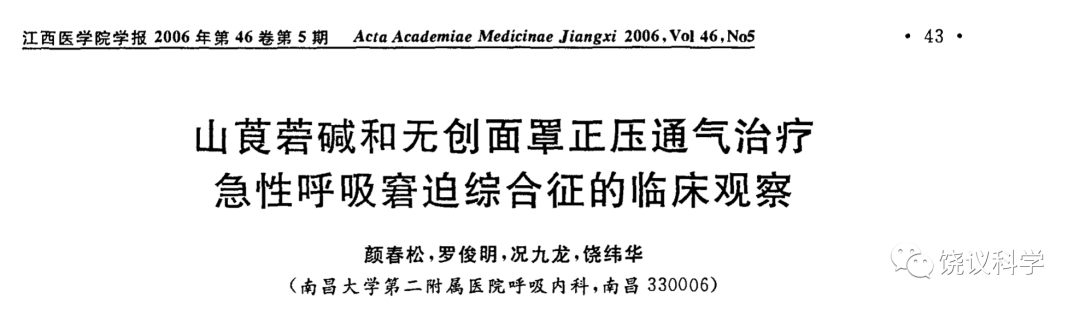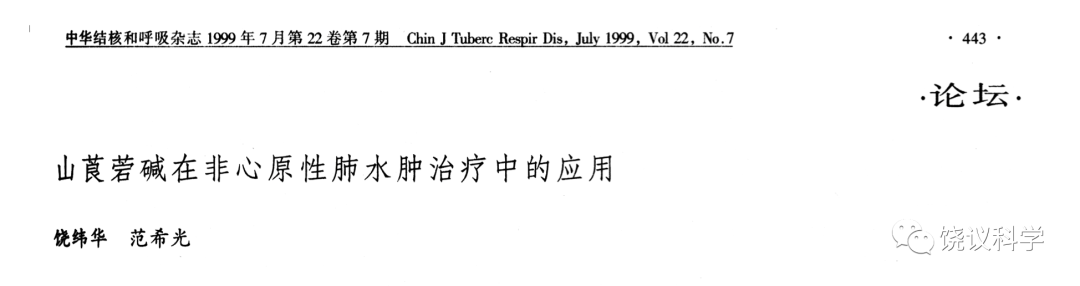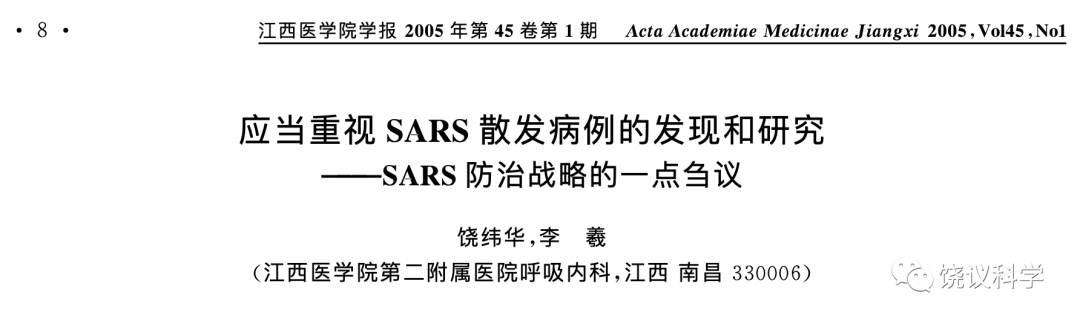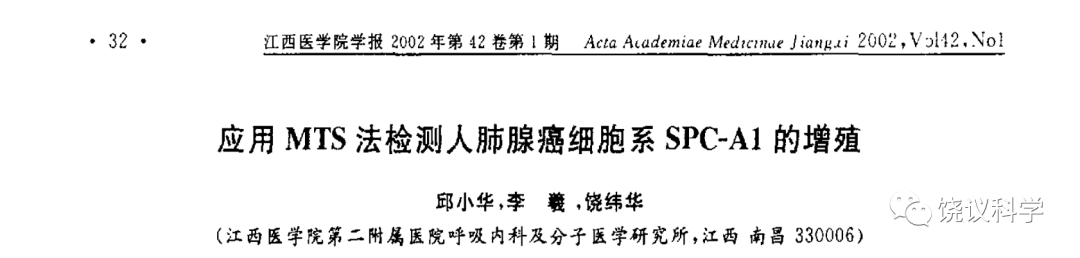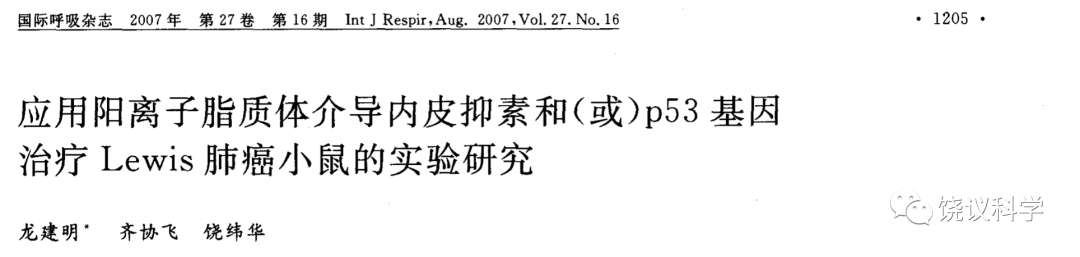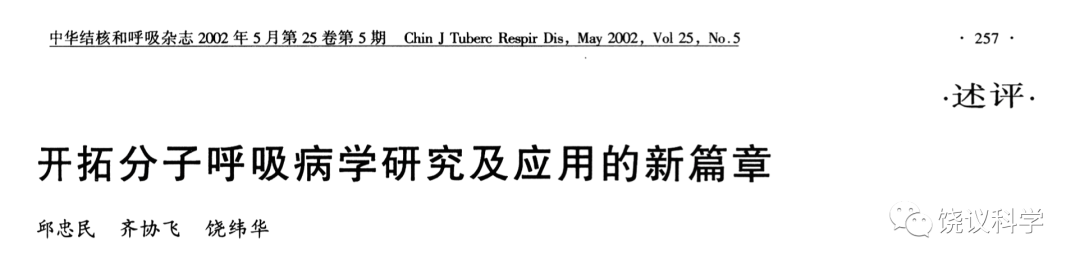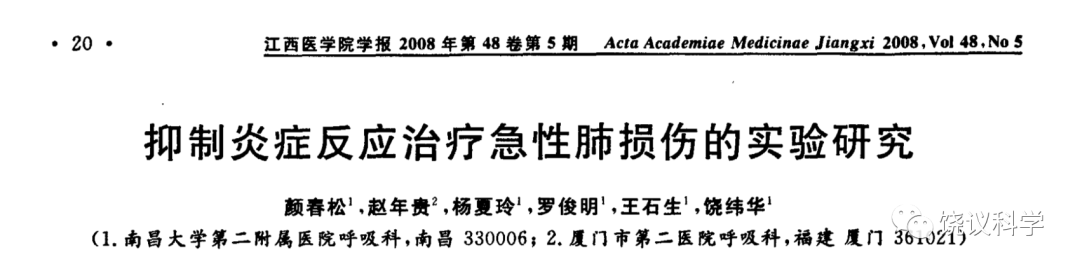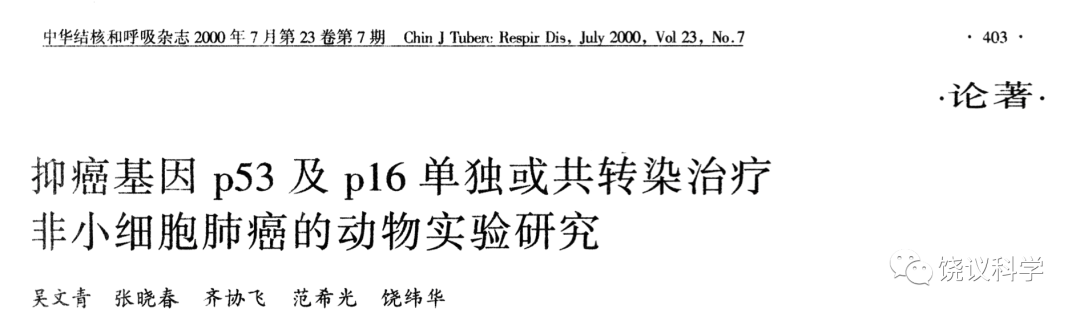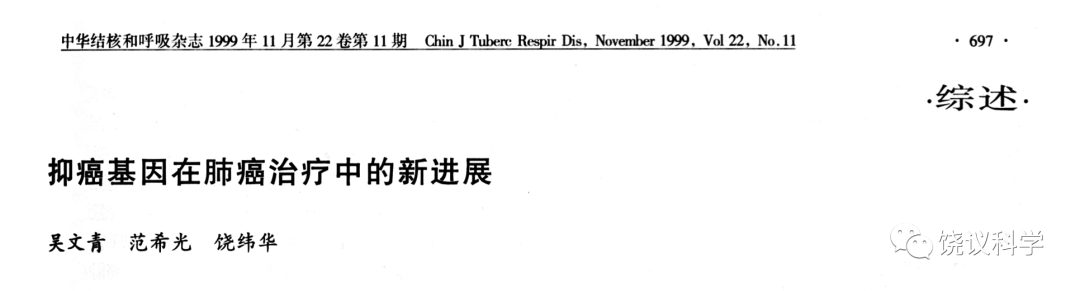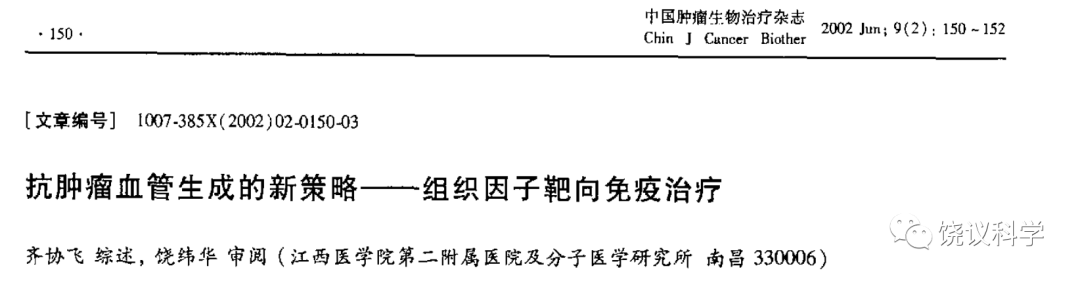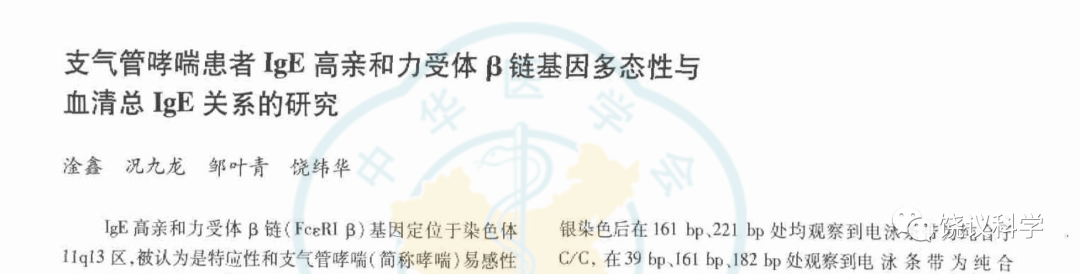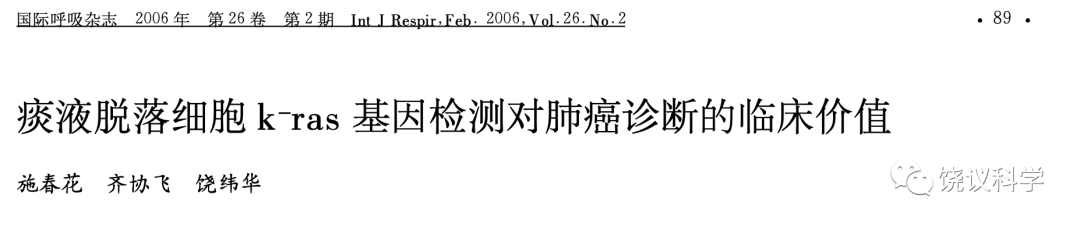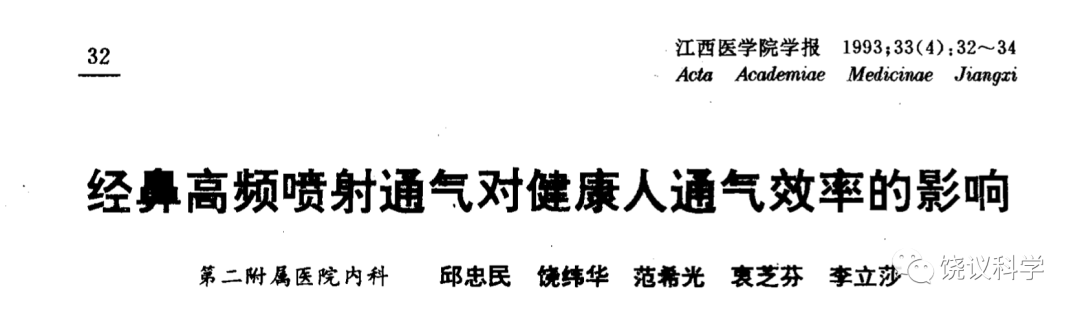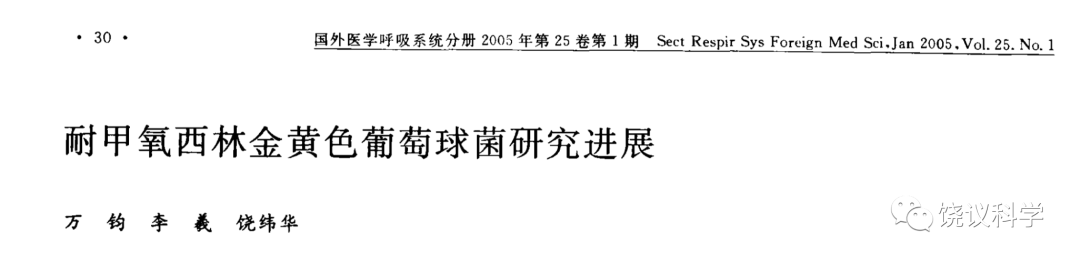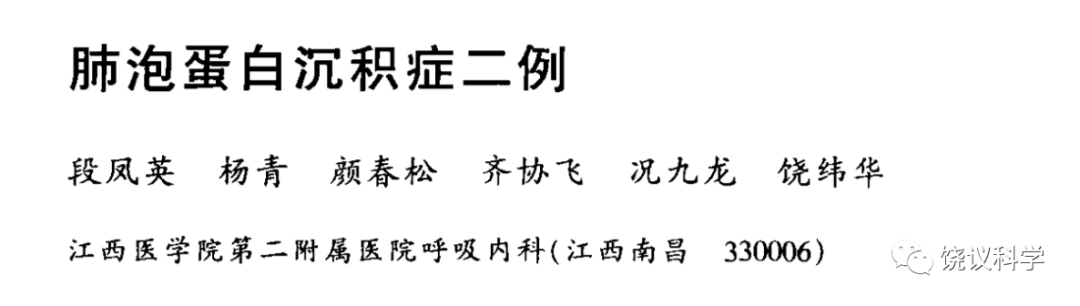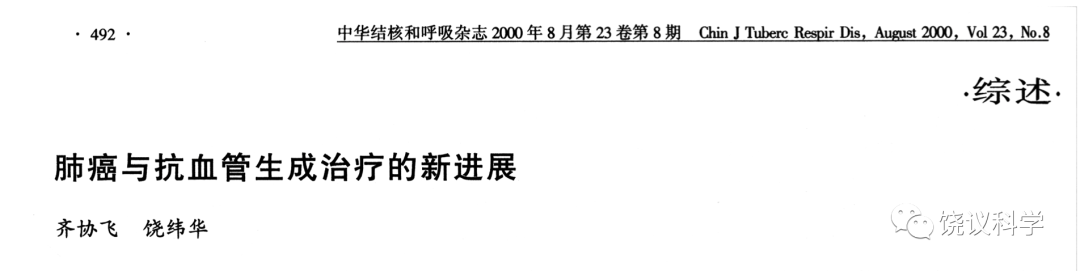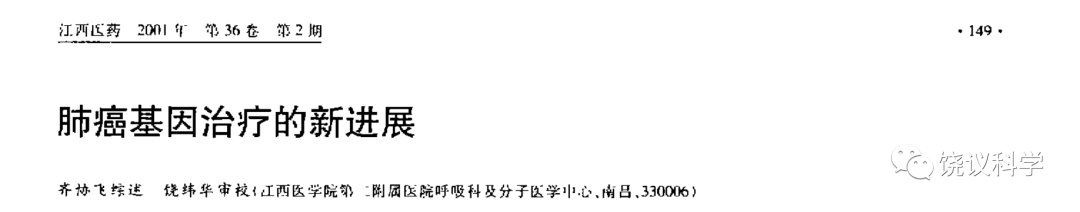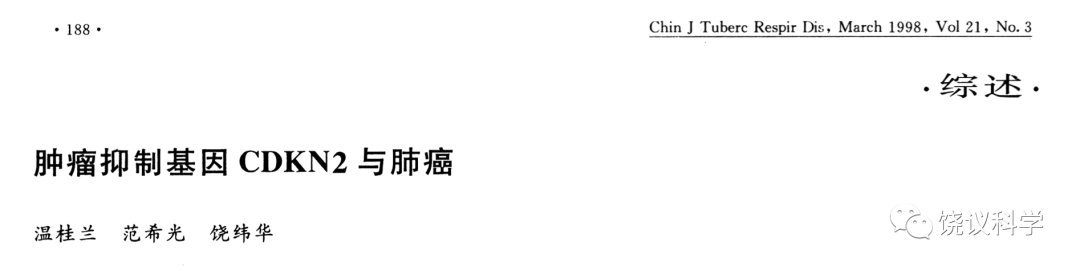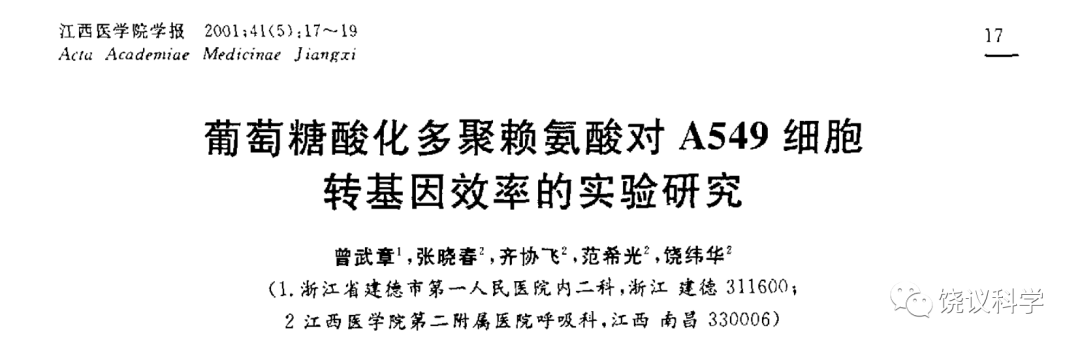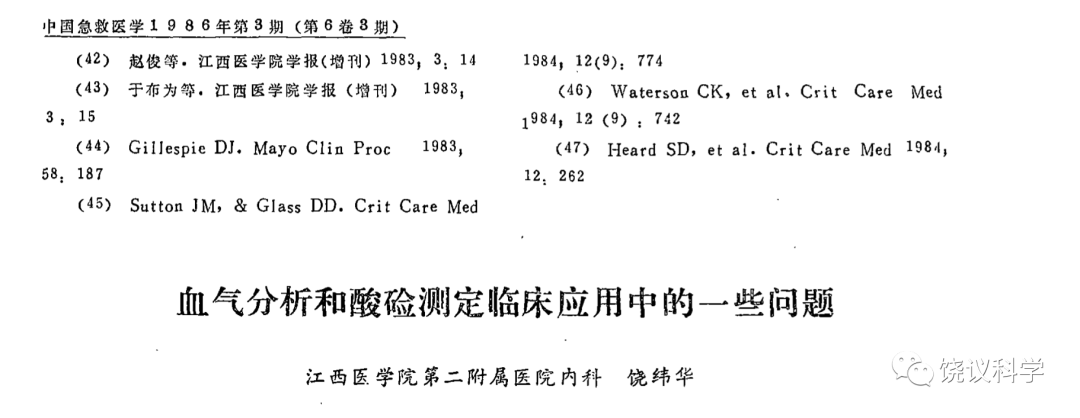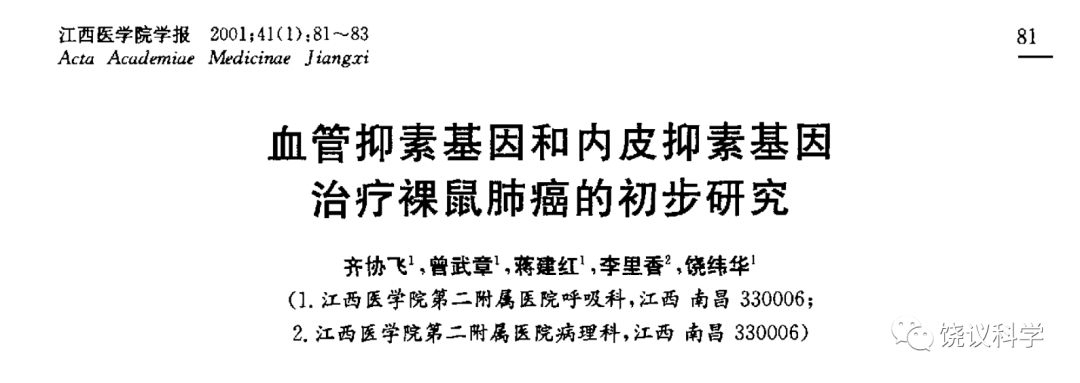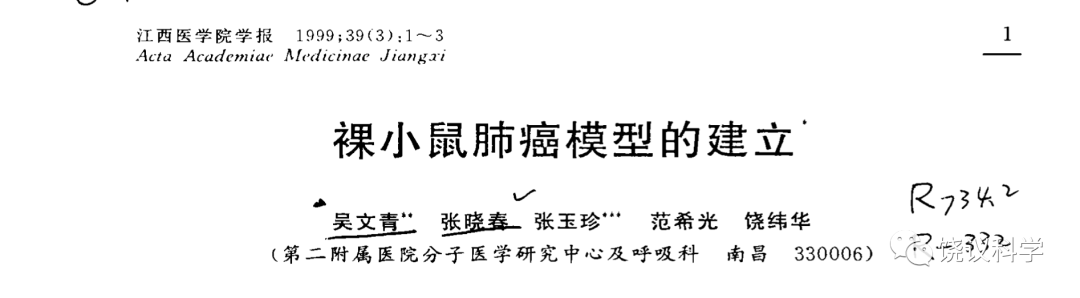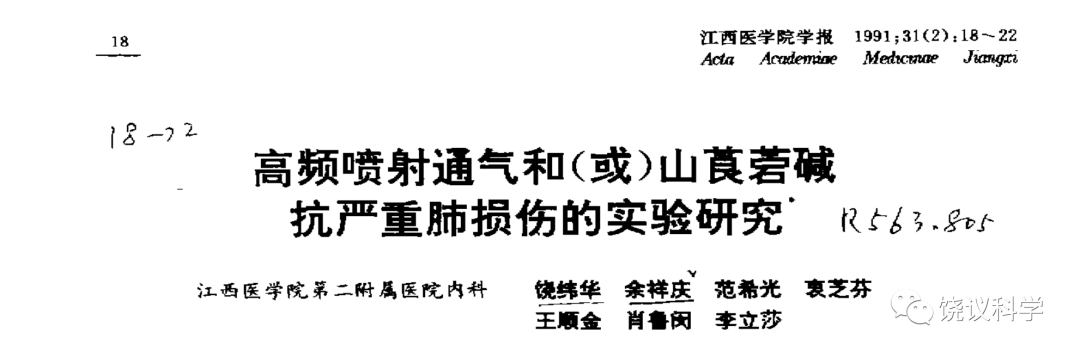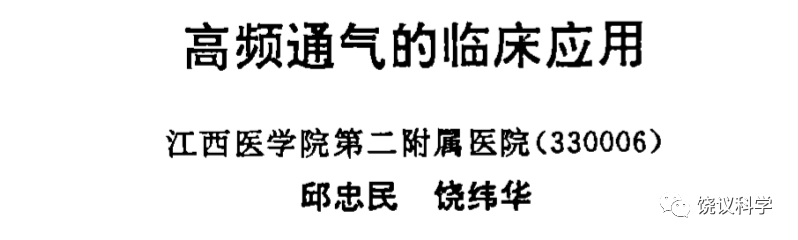父亲离世两年多。对他最简单的概括,可能是:自强不息。
父亲出生于1930年正月,1945年开始步入社会,2005年完全退休。他一直在依靠自己,努力工作,退休后还给学生讲最新医学进展、并试图在疫情中给一些在抗疫一线的医生提供建议。坚持工作可能是那一代人比较不罕见的特征。
1 父亲的家世
父亲出生在江西省抚州地区南城县。
父亲一辈子不喜欢聊天、唠家常,而他的家人很少,所以后代对此了解不多,有些也是后来猜测、拼起来。
对于父亲的祖父,我们几乎没有听说什么。父亲自己就所知甚少。
祖父在南昌工作,父亲5岁离开了南城,可能后来还有段时间去过几个月。但他的方言是南昌话,会说南城话但显然不流利。
祖父是独生子,祖母姓丁。祖母有一个妹妹、一个弟弟,弟弟后来一直跟随祖父。
祖父在南昌工作,1947年去台湾工作。父亲在南城几乎就是一家亲戚:他的舅母和三个孩子,及其后代。
2 父亲的家庭
祖父和祖母有两个孩子:父亲和他的姐姐。
父亲13岁那年,母亲去世。继母是其母亲的妹妹。后者与前夫有两个儿子,但前夫不知所踪。
1947年,祖父通过南城老乡帮忙得以去台湾铁路局工作,父亲的继母、姐姐、弟弟们都去。除了父亲因为学业没有去,几十年后才知道继母的第二个孩子也没有去、还有一个父亲的妹妹留在江西吉安。
我的姑姑在台湾与一位北京人结婚,有一子、一女。继祖母的长子曾经营企业,有成长后垮了,其子女在美国。父亲有三个弟弟,两个双胞胎分别去了美国。饶厚华毕业于台湾的药学院,首先去美国。祖父给父亲的信,有一部分是通过厚华转。厚华考了药剂师执照,结婚定居美国纽约。父亲去旧金山的时候,他还在旧金山,父亲和他们同住过一段时间。新冠流行的第一年,饶厚华在美国去世。另外一位饶兴华,我出国的时候,在旧金山郊区,与妻子有两个儿子。他们一家对我在旧金山的早期很有帮助。
3 幼年的父亲
我们所知甚少。因为父亲家人少,讲的人更少。
父亲13岁的时候,已经抗战流浪期间,父亲去泰和的省立十三中住读。带他去中学住读的高班学长走的快,让父亲记了一辈子多么难跟上。那位学长后来也学医,在军医大学工作,我读高中的时候见过。
父亲住读的第一个学期,祖母就因为普通感染去世。开始瞒着父亲,后来对父亲影响比较大。父亲青少年时代选择学医、老年选择葬在南城,都是因为祖母。
4 父亲的青年时代
1945年,父亲15岁,选择不读高中,而念专科的江西医学专科学校。1947年,父亲因为还没毕业,送家人到上海后回南昌读书。祖父、继祖母、父亲的姐姐和弟弟们经上海去台湾。
1949年,解放军进南昌后,父亲没毕业而进南昌“八一革命大学青学班”短期学习一两个月后,被分配到南昌市卫生局,工作两个月后1949年12月再到南昌市粮食局直至1953年8月。这期间与他同办公室的一位同事几十年后成为了江西省委书记。
国家急需受过高等教育的人,鼓励一些已经工作的人再读大学。父亲在粮食局期间认识母亲,并结婚。母亲一大家子人,而且有些人很喜欢聊天,家庭故事留下很多。
我外公非常寡言少语。不过,父亲咨询岳父的时候,外公提供了很重要的建议:不要继续做行政,而应该回去读大学。
1954年9月至1958年7月,父亲到江西医学院就读本科,学习临床医学。江西医学院的来源之一是江西医专,另外一来源是中正医学院。中正医学院由协和医学院的林可胜建议发起,在抗战期间与上海医学院联合办学。中正医学院一部分后来加入江西医学院、一部分成为重庆的第三军医大学(陆军军医大学)。所以,上医的沈克非等老师曾在中正医学院培养过学生,而2020年去世的中国著名心血管专家陈灏珠是中正的毕业生,然后长期在上医中山医院工作。
第二次学医,父亲年龄较大,成熟很多,因为原来上过医专所以也不需要从一年级读起,四年成绩全优,1958年为全年级第一名毕业。
但这个第一,给他带来没有预计到的伤害。
毕业时允许他有选择。他选择去江西省医学科学院(后来称为江西省医学科学研究所)。这是大跃进的1958年,江西号称要成立科学院,这是医学科学院。当时人们对于苏联的各种科学院(全苏科学院、医学科学院、农业科学院)无比崇拜。父亲被认为去了最好的单位。他到岗后,很快发现不对,江西当时根本不可能有研究条件,医学科学院是空的,不过是每天上班没有实质内容的单位。江西到1970年代有多个医学的研究所(除医科所之外,还有汪凯父亲所在的寄生虫病研究所,梅林、罗玉麟等的父亲所在的劳动卫生研究所/工业卫生研究所等,有些有事情做,但在那时设立三个研究所显然是机构太多)。父亲很快坚决要求调出,去有业务的单位工作。
1959年9月,父亲到江西省结核病防治研究所(俗称“结核病院”或“痨病医院”)工作。不仅单位比较差,而且单位领导是中专/大专毕业,他们“整”医院当时仅有的三个大学生。这个故事是大约1998年我在美国才听说,父亲本人不喜欢讲过去,所以是在美国巧遇三位中另外一位,才知道(我家与梅林家一道去迪士尼,梅林约上李晓江家,三家同行。结果发现李晓江的岳父是当年我父亲在结防所的同事)。等到1960年代初期的“食物紧张”到来,医院领导想方设法把三个大学生踢出去了。李晓江的岳父被赶到福建的三明医院工作,我父亲于1961年10月被赶到樟树的清江县医院工作。
就这样,大学毕业第一名的实际结果是到县医院工作。
5 父亲读研究生
父亲到县医院工作不久,母亲只好也准备去。我哥是1954年3月出生,因为父母都读大学,外祖母就带我哥。外祖父这时在武汉的华中工学院工作,我哥因此在武汉长大。
父亲去武汉接我哥回江西,因此在岳父那里看到不是每年都有的研究生招生信息。那时研究生不是每年都有招生,招生通知也不是到处都可以看到。
父亲决定考研究生。
而我于1962年2月在南昌出生,父亲是一边烘尿片、一边复习考研。
县医院的领导不相信我父亲能够考取,放出话来:“鸡窝里不可能飞出金凤凰”。
那时全国的研究生数量凤毛麟角,1949年至1966年全部加起来只有一万多,平均每年一千多研究生,而多数自然来自上海、北京,江西很少,而绝大多数的县医院长可能一生都没有见过研究生。
父亲居然考取了研究生,医院领导虽然没有想到,但也不反对。
因为我的出生,父亲又去上海念研究生,我哥来了江西的县城也觉得不如武汉华中工学院的校园,所以又回武汉,这样哥等于成为了我外公、外婆的最后一个孩子。年龄上,他比我们的小姨小6岁,而比我大8岁。
上海第一医学院是1920年代由颜福庆创立,其校园是1930年代建,当时是非常好的校园。北京的协和是美国人出资创办和管理,上海医学院是中国人出资、自己创办和管理。在1950和1960年代的背景是:国家对协和医学院的支持不确定(包括、但不限于部分年代不招生),迁出其中一些人,迁出其一些系科研究所,而北京医学院从专科变成本科,条件不十分好,又在协和的阴影下。
相比之下上海医学院不仅有物质基础,其领导是有眼光、有气魄、有能力、有气度的陈同生,在1950代至1960代上海医学院发展最好,明显领先全国的医学院。
我父亲入学的那年,上医招收43名研究生。大部分是上医本身系统的,包括应届毕业生(如16岁念大学、20岁从药学院毕业的桑国卫),或在上医系统工作的上医校友(如我自己的研究生导师张安中的先生陈星荣),只有三位不是上医系统的人考入当年研究生,其中两位也在上海工作,只有我父亲一人是外地考入。
我曾以为同年还有一位安徽省立医院院长的儿子,因为经常听父亲提起安徽的朱鸿良,到2022年才搞清楚朱鸿良是1964年入学,只是我父亲长期不适应上海,所以交的朋友也是“外地人”(那时上海人对外地人有很强的歧视,外地人的发音一般就是乡下人,而且上海之外的全中国都是乡下)。朱鸿良的父亲创立安徽省立医院(现在的中科大附属医院),朱鸿良在上医是著名外科医生石美鑫的研究生(石美鑫有位侄子后来是华西医院的著名院长),朱鸿良的儿子恢复了祖父的姓(林),现在安徽医大一附院,也是胸外科医生,我在2022年找到。
父亲入学后的情况,他很少说。听母亲说,他第一年遇到很大困难。外地学生,只会考试,不会读科学文献。
1950年代大学学的俄文,到了1960年代中苏关系变了,也就没有太大用处。为此,父亲刻苦学习英文,还补了日文。英文文献阅读的习惯一直保持,还能够在一定程度阅读日文文献。他发表的文章引用过日文,家里也有少量日文书籍和期刊。父亲的下一代只有英文,到了孙女才有多国语言(可以用于日常生活的英文、希伯来语、捷克语、中文,一定程度的法文和中学程度的简单西班牙语)。
父亲的研究生导师是吴绍青先生(1895-1980)。吴老先生是我国结核病和呼吸病学科的前辈。他是湘雅医学院第一届,同班有张孝骞(内科权威)、汤飞凡(著名微生物学家)等,两度留美。吴绍青曾任南昌医院院长、在重庆曾任中央医院副院长(后来这被批的时候被称为“伪中央医院”)。1957年去印度开会期间,与台湾的代表握手,也是“污点”,被上级批评。这种待遇,与我的正好相反。我回国后曾热情地与台湾地区的科学家合作,我建议我们共同发表的论文地址上台湾的不用写中华民国(Republic of China),我地址也不写中华人民共和国(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都只写共同的中国(China)。因为本来两个地址就都有中国,省去其他词,似乎非常有理(至少由我这种简单头脑看来),但立即被台湾担任行政职务的人批为“凌霸”,把我搞得一头雾水。“凌霸”一词,我以前闻所未闻,也是从这些人的公开批判里面学来的。
吴绍青因为自己患结核病而转结核为自己的专业。我父亲去做研究生之前,吴绍青已经从1950年代安排中山医院肺科开始了研究呼吸功能和呼吸疾病。肺功能部分有崔祥瑸、李华德、萨滕三等。我父亲加入这一部分。在上海期间,父亲也参与一次上海郊区某地爆发呼吸疾病的工作。
研究生应该三年于1965年毕业,但那之后留下做医生。到1968年5月,上医才记得把他重新分回江西。弟弟于1967年9月底出生于上海。
父亲到江西省卫生厅报道,立即被批评:研究生是资产阶级臭知识分子。没有留在南昌工作,而是立即分回清江县医院。
父亲6年走了一个圈,重新回到了县医院。
6 下放农村
父亲在县医院不到一年,又下放农村,到清江县三桥公社滁山大队。三桥公社是两个公社合并而成,父亲下放的地方以前称为刘公庙(后来也恢复了这一地名)。
在滁山大队,我们一家四口住在大约十几平方米的房间。2000年代,我带孩子去看过,当时还在。
一个不到40平方米的地主富农的家,被分给下放的:我家四人,比我小一岁的姜文波和他两个姐姐、他们的母亲、他妹妹等6人,两位在城里有家的单身中年人,一位正在谈恋爱的年轻人(小学的柯老师)。姜文波的父亲一直没有下放到农村,但后来与我家来往比文波的母亲还多。文波后来是央视的技术领导,我回国的时候,父母通过公开途径找到了他。文波家当时最小的妹妹与我弟弟同年。当时两个小娃娃趴在门槛上的样子很好玩。
虽然“下放干部”的目的是锻炼他们,但农村根据自己的需要。当地“人多田少”,不需要更多的下田的农民。父亲很快就成为大队卫生所的医生。虽然卫生所很简陋,农村对医生的需求并不弱。父亲很快就需要出诊。什么病都要诊治,也需要给产妇接生。开始还说不是妇产科医生,农民哪允许这种细分,各科都要做。当地给医生最好的待遇是“三个蛋一碗面”。有时晚上出诊好,农村的路还不是非常安全,包括有豺狼。
父亲除了行医,也培养了赤脚医生,有一位我们在1990/2000年代还见过,多年是当地的主要医生。
我父母在滁山大队后不久,分别调到公社医院和中学。这期间文波的妹妹掉到池塘里,滁山的信息到公社,我父亲徒步走到滁山,已经来不及了。文波一家,特别是其母亲,悲痛欲绝,成为一大伤心事。后来听说文波的母亲离开后还多年去看其埋葬地。文波的母亲后来还生了一个妹妹,起初长相非常像去世的那位。
7 回南昌工作
1972年10月,父亲回到江西省医科所。然后很快安排借调到江西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呼吸科。呼吸成为专业,当初是因为结防所,结核病最常见的肺结核,研究生考了呼吸科,以后就都是呼吸病专业。起初一年多,母亲还没回南昌,只带我弟弟回到樟树农校。我和父亲在南昌。
父亲从住院医师做起,当时做过总住院,每四天值一次夜班。这是我后来不愿意做医生的一个原因:我不过10岁/11岁,不得不一个人在家。后来当然觉得不是什么大事,但当时小孩子认为值班不人性。
他还逐渐开始研究。参加一些当地和华东片的会议。那时的打印稿是自己到印刷厂去打印。
1970和1980年代,父亲每晚的习惯是读书、读学术刊物,可能以英文刊物如Chest等为主,也有《中国医学杂志》、《中华呼吸和结核病杂志》、《国外医学》和我写不出来的日文杂志。
那时南昌不仅天气炎热,而且没有空调,父亲一边读、一边汗流浃背。我阅读科学文献的习惯,来自父亲。
那时没有晋升。上面有老医生。江西在教育和科技系统有职称晋升是在1978年之后。当时第一批晋升教授的刊登在报纸上。父亲晋升不能在医学院的医院,而需要在医科所,因为医院是兼职。医科所第一次给他晋升落后于各方面不如他的人,他非常生气,全江西在那时就没几个研究生毕业的。1976年之前江西没多少读过研究生的,读了再回江西的人那时罕见。
父亲没有读文学艺术的习惯,偶尔因为母亲家的亲戚带了,也认为所有文艺活动基本是浪费时间。
能够记得父亲和母亲同时带我们去江西艺术剧院看过一次戏,看电影是母亲带我和弟弟,或父母让同事朋友的孩子带我去。我有好几场电影(阿尔巴尼亚的、和《闪闪的红星》都是戴家三毛带我去的)。父亲年轻时有体育活动,包括打篮球,但与我们可能只打过一次。
父亲下棋也是我回国之后才与我下过(我从来下不过)。
8 访学美国
祖父在1950年代与父亲有通讯往来。而且我哥小时候生病的时候,还寄过药。但1960年代某年,父亲告诉他不行了,就断了。
1976年之后,祖父给南昌的省结防所发信,外面一封是“致启者”,大意是“犬子”某某某以前是贵院的医生,后来下放农村,能否请帮忙联系联系。里面一封信是给父亲的。信到的时候,我父亲已经在南昌工作,结防所把信转过来了。父亲泪流满面。当时在沙特的叔叔饶兴华也很快来信,不久在美国的叔叔饶厚华来信(兴华和厚华是双胞胎,在大陆出生)。由美国转的祖父信更多。
之后祖父通过香港给父亲卖过收录机等,也寄过“外汇”。当时中国外汇紧缺的出奇,外来的外汇必需成为人民币,但同时给予“外汇卷”可以在“友谊商店”购买一些稀缺商品(我弟弟喜欢的是巧克力)。
父亲的英文阅读应该挺好。但听力和口语可能是和我一道进步的。
1977年左右,母亲买了电唱机。虽然有音乐唱片,但主要是供我们听英文的。对我影响很大的是听英文的“林格风”唱片。可能因为我在1978年暑假天天听,进步超前了父亲,也可能是年龄差别带来的优势。父亲有时把自己的焦虑转到我身上,老是强调英文,殊不知我已经知道自己的英文超过他了。
我们两人每天7或9点通过收音机听《美国之音》的英文节目。从“特别英文”到一般英文。当时还有科普的“Space and Men”,也有医学进展,几乎天天是“新英格兰医学杂志”又报道什么了。
1981年开始,父亲联系出国。我看过他写的申请信,有一句是“I,51,…”(51岁的我),是我们学的林格风唱片里的一个句子。
旧金山加州大学生理系、实验室在心血管研究所(CVRI)的Norman Staub是当时大部头《肺水肿》的作者。父亲联系他是因为父亲自己用中文发表过有关肺水肿的文章。获得对方资助后,于1982年6月赴美,1983年11月回国。
在Staub实验室进行肺水肿的动物实验研究(Staub发明了肺水肿的羊模型),然后父亲还联系到旧金山总医院(SFGH),导师John Murray,观摩了临床,特别是ICU(危重医学)。ICU的一个主要方面是呼吸系统,而父亲对心血管也不陌生。
父亲在美国期间。我家变化很大。哥嫂结婚,其女儿出生,虽然他们都在武汉工作,但这些都在南昌由我母亲操办。我考上研究生。
9 回国工作
父亲于1983年11月回国。我在9月6日已经去上海读书,所以后面的事情,我直接知道的就更少。
父亲应该是这之后,才在某个时间办好全职到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的工作关系,结束兼职。
父亲可能创办了江西省第一个ICU,也应该是全国前几个。协和呼吸科的罗慰慈老师也是1983年去美国霍普金斯和Oregon,回国后创办协和的ICU,时间应该比较接近。
父亲回国后,有研究,有论文,可能是江西省在1980年代屈指可数的几位能够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的人之一。父亲教学认真,也喜欢讲课,带了一些研究生,他们后来在中国多个地方的呼吸科有贡献。有位在上海同济医院任呼吸和危重医学科主任的后来回顾道:“饶教授是我的启蒙老师,跟着他不但学回了做科研,还有临床上规范诊治病人的思维。…他留给我的,第一是治学严谨的态度,第二是力求上进的决心。同时,饶教授学识丰富,对年轻人很厚待。他总是在正确的时间,教我做正确的事情”。
1991年6月至1992年10月,父亲再次赴美。期间在哈佛医学院附属的Beth Israel Deaconess医院访问。同时自己还专门自学了分子生物学及其延伸分子医学。这当然与我当时在哈佛本部的“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系”做博士后有关。只是并非直接关系,而是他受激发,自学了相关内容。
回国后,他对推广分子医学特别感兴趣。1993年在医院建立了“分子医学研究所”,是全国最早的之一(不能排除是第一个的可能性),以后改名为现在的“江西省分子医学重点实验室”,他任主任至2005年。他发表过一些文章如“分子呼吸病学兴起”、“开创分子呼吸病学研究及应用新篇章”、“抑癌基因在肺癌治疗中的新进展”、“肺癌基因治疗的新进展”等。也在一些学术会议上讲类似内容。
2007年我回国后,当时任职北京医院任职、后任职协和医学院的王辰与他表哥来我家,进门就是“饶教授”,我以为那是我,结果是我父亲,因为我父亲1990年代提倡分子医学给他留有深刻印象。2020年,曾任中华医学会呼吸病分会主任委员、中华医学会内科学分会主任委员的301医院呼吸科教授刘又宁在报刊发表文章,写道“我对饶毅的父亲饶纬华教授也算是比较熟悉的,他是我国有贡献的呼吸学界老前辈之一,与我的老师于润江教授可算是同一辈人。据我所知,饶纬华教授早年也曾在国外留学,专研过分子生物学,也是在我国呼吸学界最早提倡开展分子生物学研究,并举办学习班传授研究手段的专家”。
第一次非典肺炎(SARS)发生过后,我父亲多篇文章表达了一个意思:散发的规律不清楚,可能会再发。
这是其中一篇文章的截屏:
图片
新冠肺炎流行后,他坚持认为这是证明了自己的观点(对此,我不加评论)。
父亲到2005年离开医院之前,长期坚持医疗、教学和研究并重,是真正的医师科学家。
新冠初期的2020年,父亲多次要我给王辰、乔杰等转到他对于肺炎治疗的建议,我奉命转达了。
4月,他对肺炎有一段评论,我正好录像了。
后来,厚华因为新冠去世,父亲深感意外。再后来,他在旧金山总医院进修的老师在巴黎逝于新冠,父亲感觉也不好。
父亲是新冠期间腹痛去医院,他以为是胆囊炎,因为症状不重,而且没有肝脏的症状。结果第一次检测就是很大的肝癌,只是所在部位碰巧较少引起症状。家人没有告诉他,直到手术之后。他认为创面太大,才告诉他不是胆囊炎,而是肝癌。这样在相当长时间,他没有特别紧张。
我弟弟辞去美国的教授职位,全职回国任职南方科技大学医学院生物化学系。
父亲和母亲去深圳住了几个月,前面毫无症状,和弟弟在深圳一道生活非常高兴。
肝癌复发后回北京治疗。他自己对于病情的进展比较清楚,要求五一前后回家住,全家回来。五一假期的后期大出血,不得已只能再住院。2021年5月21日丧失知觉、23日凌晨去世。
10 父亲与我
2007年之后,父母大部分时间与我和儿子住北京。
对于身后,父亲属于不太在乎的那类。工作是说过退休后要写回顾,但一页纸都没有写完就停笔了。我的老师张安中也曾经说过要写一本被郑念《上海生死录》更好的自传体书,也没有写。大舅喜欢文字,而且写了一百多页,但写到接近需要写初恋的时候,停笔了。
我估计,按父亲的能力、坚持和两耳不闻窗外事的集中精力,他一直认为如果有我的条件,在事业上会比我做得好得多,从而非常有道理地认为我浪费了很多时间,也就是说他基本对我非常失望。
...........................................................................
附一: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的饶纬华悼念文章
呼吸科专家饶纬华:行医唯诚 教学唯真 研究敢想
我国呼吸系统分子医学的先行者、我国呼吸病学界著名专家、江西省呼吸病学界医疗、教学和科研领袖饶纬华,2021年5月23日凌晨因病医治无效,逝世于北京,享年91岁。全国政协副主席邵鸿,中国医学科学院院长、协和医科大学校长、国家呼吸医学中心主任王辰,中国医学科学院、协和医科大学党委书记姚建红等以个人名义送了花圈。
饶纬华教授常说医生要做到“一生努力,两袖清风,追求卓越,攀登高峰”。2014年,饶教授为江西省分子医学重点实验室题词:“敢想敢闯,唯诚唯真”,这不仅他是对医学科学研究后辈的勉励,也是他自己在医学科研和为人为师方面的写照。王辰教授称饶教授“是上世纪八十年代我从临床医生中听到关于分子生物学介绍、议论并努力应用于临床研究实践的第一人”。
饶纬华教授曾在江西省立医学专科学校学习,于1954年至1958年在江西医学院临床医学系学习。1962年考入上海第一医学院研究生,师从中山医院一级教授、著名呼吸病专家吴绍青教授。1968年下放江西农村,做过乡村医生、公社卫生院医生、县医院医生。1972年回江西省医学科学研究所工作。1975年至2005年在南昌大学二附院内科工作。1982年至1983年在美国旧金山加州大学医学院,先后随心血管研究所Norman Staub实验室进修疾病的动物模型实验研究、随旧金山总医院John Murray进修呼吸和重症医学。1991年至1992年访问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院附属Beth Israel Deaconess医院。饶教授曾任江西省分子医学重点实验室主任、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大内科副主任、呼吸学组组长,中华医学会江西分会呼吸病专业委员会第一、三、四届主任委员,华东地区呼吸病协作组组长,《中华呼吸与结核病杂志》编委、资深编委。
饶纬华教授一身正气,崇尚医道。他因幼年时期母亲逝于常见病而学医。成为医生后,他坚守“救死扶伤”的神圣职责,把病人当亲人把解除患者的痛苦看作是自己最高的追求,亲历亲为治病救人直到75岁。几十年为大量病人解急救难,无论是春夏秋冬,还是白天黑夜,只要是患者需要,他有求必应。他常告诫年轻人:“做一名好医生,要有高尚的医德、精湛的医术和艺术的服务。三者缺一不可,三者都是无止境的。”在他从医近60年的职业生涯中,不为名、不为利,一片丹心为病人,一直坚持深入病房,认真观察病人病情,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他对患者高度负责,只要有百分之一的希望,他就要尽百分之百的努力,想方设法救治和解除病人的痛苦。80年代初,一位伴有呼吸衰竭、严重感染支气管扩张患者突然停止呼吸,开放气道,人工呼吸在当时条件下首选,但由于患者肺部严重厌氧菌感染,其痰奇臭无比,没人敢做口对口人工呼吸。饶教授看出大家的顾虑后,亲自进行人工呼吸,在他的带领下,患者呼吸复苏成功。饶教授以“德高医精”为座右铭,爱岗敬业。他优良的医术、丰富的经验、高尚的医德和精良的医术赢得了病人发自内心的尊重和赞誉。
饶纬华教授学识渊博,天下桃李。饶教授是学生心中令人尊敬的长者。饶教授常说,“教师必须要规范自己的言行举止,要以自己的‘言’为学生之师,‘行’为学生之范,言传身教,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导之以行,做名副其实的人类灵魂工程师”。他常教导研究生:做学问首先要学会做人,对人、对事要诚恳和踏实,对名和利要淡薄和轻视。饶教授一生执教,桃李满天下。早期的青年医师和他指导的研究生现在不但已成为本省本专业的学术带头人,在国外和其他省市工作的也都成为当地的学科带头人。在医学授课和临床教育,他非常有感染力。在介绍国际医疗和医学科学前沿知识方面,他的讲学效果特别突出。他对后辈在工作上要求严格,生活中和蔼可亲。他要求优秀的年轻人多读书、多学习、多做事,要临床、科研、教学全面发展。他乐于助人,不仅对自己的研究生,有些没有成为他研究生的学生也认为“是他让我真正走上呼吸专科之路”。 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他开创了全省最早的呼吸监护病房,为我省重症医学奠基人。他率先在省内开展危重病人的救治及呼吸支持专业技能培训,培养了大批省内外呼吸与危重症知名专家、学者和医生。他主持并承办了全国性分子呼吸病学培训班等十余次,带领江西呼吸系统教学和科研事业走向全国舞台。饶教授的一生都在传道授业,即使退休多年,回访医院时仍然讲解最新科学进展。
饶纬华教授追求卓越,刻苦治学。他长期坚持临床与科研并举,聚焦国际医学科学研究前沿,对医学科学发展有前瞻性。他在非心源性肺水肿、急性肺损伤、氧化应激与呼吸病、呼吸病分子生物学研究等领域开展了大量的临床及科研工作。以其缜密的科研思维,积极的探索精神,在临床研究和实验研究有多年的沉淀和积累。在引进高频通气后,为探索其临床生理,进行了两百多例次狗的试验,并在动物及人体进行了I型及II型呼衰,控制呼吸时的效益和问题的研究,指明了这种简易呼吸机工作原理、效果和局限性。在肺水肿方面,饶教授自己和团队用Staub教授的绵羊肺淋巴瘘模型研究中国药物山莨菪硷开始,连续16年从基础到临床,全面探索了山莨菪硷对各种类型非心肺性肺水肿的疗效、特点、作用机理,并提出了临床应用的指征和方法,提出了三种方案,也提出了问题。实现了研究和转化应用。在分子医学方面,饶教授于1993年创建了江西省分子医学重点实验室,在国内率先开展了基因诊断、基因治疗和免疫细胞为肿瘤浸润淋巴细胞的治疗等研究工作。明确可定性和定量对病毒性疾病和遗传性疾病进行基因诊断显著优于其他方法,落地DNA亲子鉴定及脏器移植的HLA分型。探索了P53、 P16、P21、B7等基因与肿瘤治疗的关系。2003年SARS暴发时,探索了临床表现酷似SARS,但没有人对人的传染性,即散发型SARS。提出了“两种流行” 、“两种病株”的概念。饶教授为江西省临床和基础研究创造了良好条件推动了临床医学各大专业科室科研工作的有效发展,开启了江西省临床医学科学研究新时期。
饶纬华教授于1986年获得了首届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资助,成为南昌大学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的第一人。他作为项目负责人多次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和省科学基金。他发表了近百篇论文,其中30多篇发表在国内专业界的主要刊物,30多篇在华东地区及全国专业会议上作过专题报告。
饶纬华教授的一生,是探寻真理、不断奋进的一生,是为呼吸系统疾病救治事业不懈奋斗的一生。他为人师表、治学严谨,勤勤恳恳、任劳任怨、正直坦荡、精益求精。作为名医,他时刻不忘自己的使命,他的道德境界和人格风范,他“孜孜不倦地追求学术,格物致知”的精神值得我们尊敬、学习和怀念。
附二:饶纬华教授的学习和工作经历
1945.8-1949.7江西医专 医疗系
1949.7-1949.8 南昌八一革大青学班 学员
1949.9-1949.11南昌市卫生局 干部
1949.12-1953.8南昌市粮食局 干部
1954.9-1958.7江西医学院 医疗系
1958.9-1959.8江西省医学科学院
1959.9-1961.9江西省结核病防治研究所
1961.10-1962.8江西省清江县医院
1962.8-1965 上海第一医学院 肺科研究生
1962.9-1968.5上海第一医学院中山医院医生
1968.6-1972.9江西省清江县医院、公社、大队、生产队
1972.10-1975.4江西省医学科学研究所
1975.5-2005.8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呼吸科/江西省分子医学重点实验室1982.6-1983.11 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 心血管研究所
1991.6-1992.10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院 附属Beth Israel Deaconess医院
附三 饶毅:2016年复旦大学研究生毕业典礼上代表校友致辞
与困难共舞
--复旦大学2016年研究生毕业典礼校友致辞
首先我要感谢复旦大学的包容:允许我因为上海第一医学院并入复旦而成为校友。
其实,即使上医,我也没毕业。无论复旦还是上医,称为母校,对我不最合适。更合适的称呼是:父校——我父亲的母校。
五十四年前,我父亲考入上海第一医学院,与大家一样在此完成了研究生学业。今天我与大家分享我父亲的故事,因为他与在座同学贴近,父亲是在这里开始知道什么是医学科学、如何进行科学研究。感恩复旦暨上医为我们两代提供了高等专业教育和训练机遇。
在毕业季,
你们中间无忧无虑者,须知:困难在人生中本是常态;
你们中间忧心忡忡者,须知:坚毅在进化中嵌入基因。
1968年离开上海的父亲,无法像今天的你们一样怀揣梦想、期待充满阳光的未来,因为浩荡的历史带给他的是事业“塌方”:父亲回到江西很快被从南昌送到县医院,而县医院也不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认为父亲受教育过多而应该去农村劳动。离开人才济济、良医众多、设备优良的上医不到一年,父亲的工作地点变成了偏远农村的卫生室,那里的医生只有父亲一人。
你们可能不会有“断崖式”转折,但你们也会有不得不与困难共舞的时候,我期待你们:
在逆境中舞出情怀,
在顺境中舞出精彩。
当年,父亲除了似乎一辈子要生活在农村的前景所带来的精神压力之外,还面临其他问题:人们生病没有昼夜,父亲是全天候的医生;农民不可能分科,父亲只能从一位呼吸内科高度训练的专科医生,几乎被磨炼成“全科”医生;出诊远近村落、跋山涉水都靠双脚;一家四口的居住面积不到十平…。
父亲曾半夜长途步行赶到农民家里为难产的孕妇接生;挽救故意或误服农药的村民;口对口呼吸救助溺水儿童…不可能都靠现代医药,也试过草药。广阔的农村,成为父亲的临床实践基地;缺医少药的农民触发父亲培养当地青年成为赤脚医生。
在条件很差的上世纪七十年代,他回到南昌不久就努力从事医学研究。八十年代,他从美国引进现代医学研究方法。九十年代他更好地理解了优美的DNA双螺旋和重组DNA技术带来的生物医学革命,将临床医学与分子生物学相结合,探索疾病诊断和治疗,推进分子医学。
虽然五十年前不同于现在,但今天的世界也疯癫,今天的中国并非天堂。在与大家分享了五十年前毕业的研究生如何与困难共舞后,我衷心祝愿你们:
人生穷乏处,达观自爱,追求崇高,不在乎得失,只要境界脱俗;
人生得意时,忧乐天下,正道直行,不在乎伟大,只要乐在其中。
附四 饶毅:2019年首都医科大学开学典礼致辞
得到孩子的尊重
今天,我们请首都医科大学著名校友王辰给各位新生致辞,既是对王辰学长的尊重,也代表我们首医师生员工比较大的愿望,希望有朝一日:协和医学院以及其他医学院校都由王辰学长等首医毕业生带领其发展。
我自己有一个小的愿望:希望各位新生通过自己的言传身教,最后被你们自己的孩子特别尊重。
我自己的父亲是医生,而我小时候不太懂事,不知道充分尊重医生,经过事实的教育才对医生特别尊重,到现在,我有些后悔自己没有从事医生的职业。
35年前,父亲和我在上海乘公交车时,有位乘客突然倒地不省人事。佩戴医学院校徽的我束手无策,而父亲立即救助,病人得到缓解。此后,我再也不敢佩戴校徽,也不敢印名片。28年前,父亲第二次到美国,回国后建立可能是中国第一个分子医学研究所,也在全国呼吸病会议上讲分子医学、在《中华结核与呼吸病杂志》撰文介绍分子医学。我回国后,王辰第一次到我家找“饶老师”,我以为是找我,但他的眼神聚集在我身后:我的父亲。
这些故事似乎是我在赞扬自己的父亲。其实不一定,各位新生应该视我为“医生的儿子”,也就是你们自己儿子的代表。我不过是年资高于你们一般还没有出生的孩子们。所以,今天是帮你们的儿子、女儿拟草稿,以便几十年后他们的代表来首都医科大学,或者去协和以及全中国其他医学院,赞誉你们的人生和事业。
附六
2016年复旦大学研究生毕业典礼致辞的英文翻译
Dances with Difficulties
--Speech at the 2016 Commencement of Fudan University
Yi Rao
I am grateful to the inclusiveness of Fudan University in considering me as an alumnus merged from Shanghai First Medical College(Shangyi).
In fact, I have not even graduated from Shangyi. For me, it is not the most appropriate to call Fudan or Shangyi Muxiao (mother school). It is Fuxiao (father school)—my father’s school.
54 years ago, my father entered Shangyi, and, like all of you (but not myself), graduated from here. Today I would like to share with you what I have learned from him, because he is similar to you and he started to know what is medical sciences and how to perform academic research. My father and I would also like to take this opportunity to express our gratitude for the advanced education and professional training Fudan/Shangyi has provided to two generations of our family.
When he left here in 1968, it was impossible for him to imagine a future full of sunshine, because catastrophic historical events had swept him as well as more than a billion other Chinese. To put it mildly, his career collapsed. Once he was in Jiangxi, he was quickly sent from Nanchang to a hospital in a small town, which also deemed him to be over-educated as a “bourgeois intellectual” who had to be educated through labor in the countryside. He was soon sent to a small village, transiting within less than a year from the Shangyi with many excellent doctors and nurses and medical equipment to a single room clinic, with the only doctor being him and himself.
In addition to the psychological shadow brought by the prospect of living a rural life forever, my father faced other problems: people got sick day or night, he could only be an all-time doctor; peasants did not distinguish between medicine, surgery, pediatrics, obstetrics or gynecology, he was transformed from a highly trained doctor specialized in respiratory diseases to an all-around doctor;with neither cars nor bicycles, he visited patients by foot, to villages close or afar, crossing ditches or creeks or mountains; our family of 4 lived within less than ten square meters…
He walked at midnight to help a pregnant peasant deliver a baby safely when it was dangerous. He brought back to life those who knowingly or unknowingly took pesticides. He did mouth-to-mouth resuscitation of drowned children. Not all his work was assisted by modern medicine, he had tried local herbs.
Along with his own practice, my father educated young locals to be “bare-foot” doctors, maximally lengthening the period of improved medical conditions in the rural areas.
In the 1970s when conditions were poor, he tried hard to carry out medical research after returning to Nanchang. When more opportunities arose in the 1980s, he introduced modern research approaches from the US. In the 1990s, he appreciated the beauty of the double helix of DNA and understood the biomedical revolution ushered in by the recombinant DNA technology. He even combined molecular biology and clinical medicine, established an institute of molecular medicine, and explored new ways for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of diseases.
Your era is different from that of 50 years ago, but the world today can be insane, and China is not definitely the heaven. Your life will also run into problems and difficulties, but hopefully not of the cliff-jumping type. How to dance with difficulties will also be of concern to each of you.
I sincerely wish that you can
dance with grace when the sun turns away,
dance with compassion when it shines your way.
附七 父亲部分研究论文